
艺术拼贴 不是为了从生活现场撤离

《阿波隆尼亚》剧照
大量西方当代戏剧的涌入,呈现种种怪模怪样的形貌与陌生的舞台语汇,令人惊艳,也令人迷惑。这是文化差异、语境不同的必然结果,也与人生经验积累和对后哲学思潮认识不足有关。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权力中心从欧陆转移至美国,古老的经济版图一再改写,苏联解体后欧洲知识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危机。历史的线性进化论已被打断,同一性、整体性的神话断裂成无数的碎片,神、上帝、善的形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统统失去对人们思想的支配,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叙述——拼贴、反讽、间离、荒诞……悄然兴起。
异质拼贴制造不确定的感觉结构

《信任》剧照,图源网络
去年夏天,柏林邵宾纳剧院在天津、北京演出的《信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文本的拼贴与不同媒介的拼贴;一是凸现表演层面,让现实主义戏剧隐身在角色后面的演员现身,并将扮演性变成一种叙述手段。演出中,表演者(演员)拿着话筒直接面对观众,大段大段地近乎独白地诉说:“我告诉你……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不告诉你……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离开你/我不离开你/我收拾行囊/我爱你/我吻你/我碰触你/就算我真的想要你……(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在仿佛停不下来的诉说中拼贴了大量语无伦次、言不及义的废话:“时间的形状/洗盘子的真相/一个免费的电话/带给你免费的选择/吃小吃的艺术”……夹缠着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表述:《拯救现代的灵魂》、《商品美学批判》、《超文化主义》、《崩溃的体系》……
在被剪碎的东拉西扯中,闪闪烁烁地浮现零散场景和人物,如“凯”,“一个英俊、高大、十八岁的金发男孩”……观众依稀可以辨识出一个胡乱花钱、随意跟男人上床、醉态蹒跚、说话颠三倒四的女子,一个十四年前被家庭抛弃、如今又被社会抛弃的男人……这类相关的人物,相关的生活细节,作为“戏剧性戏剧”的残留物,是在密集、狂乱的语词之流夹带出来的,是被演员讲述而不是被角色表演呈现出来的。
与此同时,演出充斥着大量的、狂乱的舞蹈/肢体动作。舞者/表演者激情四射的旋转、扑跌、堆叠、拉扯、冲撞……除少数舞句的不断重复和个别特别设计的形体造型外,狂乱无序的肢体呈现包含大量的临场即兴。肢体动作盲目而混乱的随机性,冲毁了意识独占的地盘,解放了自身的能量。这是一种无定向的动作之流,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结构,一种自我缺失的迷醉与晕眩。
语词碎片与凌乱动作,异质拼贴,相离相荡,思绪散漫无归,意义似有若无。一具具不安的身体无定向的躁动,与意义空缺的语词倾泻所产生的空虚感,将当代人的身体与头脑一并掏空。
拼贴是为了将焦点引向现实世界
今年6月,波兰华沙新剧团在天津大剧院演出的《阿波隆尼亚》,复杂的后现代拼贴与自我解构,给观众造成观赏障碍,不是看得一头雾水,便是借助阐释活动的元语言集合强行挤压出“苦难”、“牺牲”、“弑母”的重大主题,却忽略了其解构的自我背叛、自我颠覆——既颠覆传统戏剧的叙述模式,也解构“牺牲”的传统意义。
《阿波隆尼亚》全剧包括开场白和两大部分。编导者大量挪用《阿伽门农》、《俄瑞斯忒斯》、《阿尔刻提斯》等希腊悲剧的相关场景与角色身份。这种挪用,不是为了让观众领略悲剧的崇高,也不是为了凸显悲剧英雄与命运抗争的意义。不同场景的挪用,不同人物的牺牲,只是一个将焦点引向现实世界的话题。从人性的黑暗与历史的残忍这一角度看来,所有的牺牲,杀与被杀,都毫无意义。
编导者不制造任何幻觉,舞台就是演员表演的场所。演员穿着现代服装,拿着话筒、摄像机、电视遥控器,操弄木偶……角色与角色扮演者同时现身。戏剧文本舍弃因果关联的情节结构,在历史资料(阿波隆尼亚为掩护犹太儿童而牺牲的史实、二战中东方前线丧生和种族灭绝的人数)中,拼贴了大量古希腊悲剧的碎片、泰戈尔剧作《邮局》的片断、卡夫卡的小说《学院报告》、安徒生的童话《母亲的故事》、犹太裔作曲家安格尔·柴可夫斯基11岁时写给母亲的诗……众多叙述线索交叉穿插,整出戏成了一座小径分岔的叙事迷宫。
演出时,舞台被分割成多个表演区,一个小型乐队(歌手、鼓手、吉他手等)始终在场,即时录/放像将戏剧场景剪碎成局部特写或空镜头,演员与角色毫无过渡地快速转换,现实与虚构混同,使传统的叙述结构宣告崩解。观众茫然无序地跟着演员表演或屏幕影像,一同陷入拼贴世界特有的分裂状态中。
编导者宣称,他们意在挑战罪恶、公义和罪恶感等“万事的定义”,人类、神明、英雄、受害者和刽子手,将在他们所提供的平台上交会、碰撞。只是其所携带的意义,不是明晰的,而是含混的。你可能有所意会,却又难以说出。这难以解释又吸引你想去解释的空白,是编导者、演出者预留给观众思考的宽阔空间,也可能是连编导者、演出者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阐释陷阱。
解构的同时在建构
先锋艺术家认为,后现代拼贴是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重要分野。既然现实本身就不完整、不统一,拼贴恰好让人们窥见一个传统艺术千方百计掩藏起来支离破碎的真实世界。后现代艺术家相信,拼贴潜含某种激进的政治功能。它使艺术家舍弃那些长久以来被当作思想准则、艺术准则的教条,摆脱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神话,看清传统形而上学的盲点。然而一旦后现代拼贴将否定性批判推向极限时,也可能自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沼而自行解构。以《信任》一剧为例:《信任》是当代德国炙手可热的中生代编导李希特(F.Richter)与荷兰编舞家阿努克·范·迪克(A.Wan Dijk)2009年共同创作的作品。作品试图呈现在当代经济危机、精神危机的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与信任危机。信任?信任谁?信任什么?广告?媒体?政治宣讲?明星代言?在这个充满谎言与欺骗、有时连自己都无法信任的世界,“信任”与其说是一个疑问,不如说是一种反讽。然而,疑问仍在,作为观剧的观众,我们能信任《信任》吗?
拼贴在艺术史的诸多阶段都有。它是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段,却没有具体的路线图。它可以是一种精心的设计,也可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堆砌。成功的戏剧拼贴,断裂的叙述线索不只存在分岔与空白,也存在隐而不显的联结点。不是为作品预设联想与解释的方向,而是为了引起间离与震惊,在解构的同时也试图去建构。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难》(1938年)、彼得·魏斯(Peter Wejss)的《马拉/萨德》,到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的《哈姆雷特机器》……拼贴戏剧的建构一直在路上。
大多数艺术家缺少学识与勇气
我们无须盲目崇拜西方,近年来汹涌而至的西方戏剧,良莠混杂,不少演出只是西方舞台上的二三流作品或小打小闹的实验小品。像《安魂曲》、《群魔》、《伐木》、《亨利四世》一类的佳作并不多见。但总体而言,西方当代戏剧的现实感较强。你可以对当代人的精神焦虑与信任危机表示不同看法,也可对挑战“万事的定义”不以为然。但像《信任》、《阿波隆尼亚》这样的作品,编导者对艺术的探询始终与对现实生活的探询紧密相关。对他们来说,舞台实验所追求的,不仅是种种更新戏剧叙述的方法,也是更新理解人性、历史、生活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这里,舞台上不同文本、不同媒介的拼贴,早已见怪不怪。不明就里的演员表演与现场即时录/放像的拼贴,已多到成了俗滥的陈套。新近公演的《从前有座山》、《拥抱麦克白》,更是随兴所至地将舞台拼贴玩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虽然制作方、编导者也有一定的创作方向与意义追求,但散乱无归的演出,只是不知所云的炫技与拼凑。我们的艺术家并不缺少智慧与灵气,缺少的是学识与勇气。当代优秀戏剧的力量,既在哲学与叙述学,也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在政治生态与商品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我们大多数艺术家已从生活现场撤离。戏剧创作除了老调重弹和玩玩花活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更多精彩: 《凯风智见:雍正帝坠泪的惨败——血战和通淖尔》
《凯风智见:礼物的炮灰——春秋战国的刺客们》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河北累计争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56家
-
深圳真金白银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活水
-
山东中小企业多项指标全国居前
-
助力企业加快拓展海外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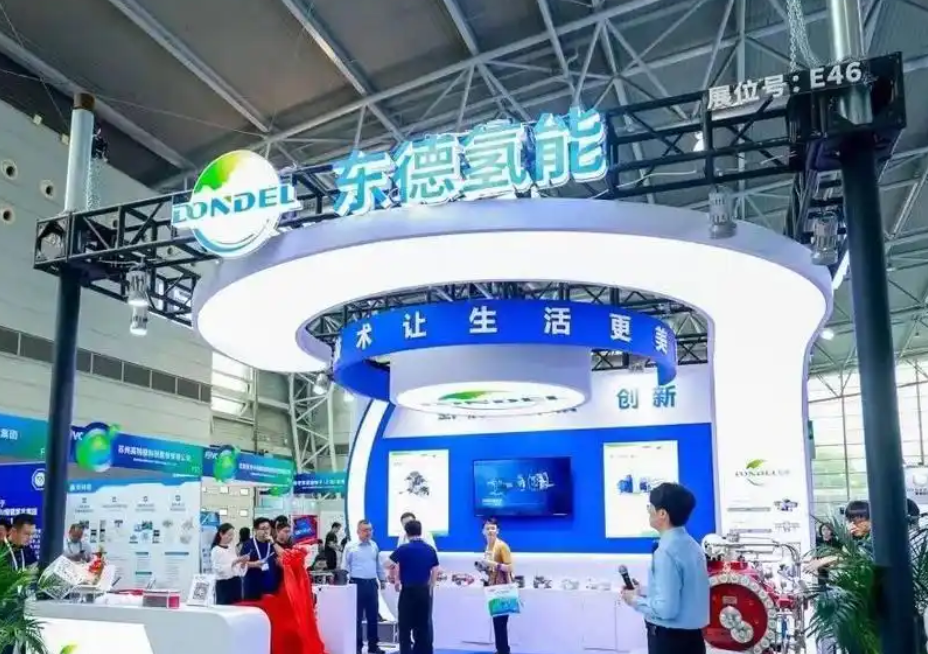

 热点新闻
热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