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戰史中探尋勝戰智慧
原標題:從戰史中探尋勝戰智慧
●從歷史的真實中尋求感悟,激發基於新的時代條件的創造性思考。
戰史研究作為歷史研究的一部分,一直非常重要。《管子》說:“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戰爭是活力對抗,戰爭史既可揭示規律也顯示著或然性,既包含著科學更包含著藝術,既有經驗更有教訓。
當前,世界范圍內科學技術多域競發、交叉聯動,強力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發展。在這當中,人工智能以機器學習的進步為突破,迎來第三次大的發展,人工智能的軍事運用將會改變戰爭形態,改變戰爭制勝機理。長遠看,未來大量智能無人系統投入戰場,將改變很多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信息化戰爭、局部戰爭的情形,出現新質作戰力量、新的作戰樣式和新的攻守戰法﹔未來戰爭中打仗的士兵看不到對手流血,不打仗的老百姓卻在電視和手機上直視殺戮,等等。這一系列重大變化,必然帶來一系列重大問題。未來戰爭到底怎麼樣?我們該如何認識和駕馭未來戰爭?
這使我們想到了歷史上的諸多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也包括一系列重要的局部戰爭。因為世界大戰是全球規模的戰爭,是全社會總體力量綜合較量的戰爭,是深刻改變世界發展進程的戰爭﹔因為局部戰爭更多體現了政治對軍事的掌控,體現了戰爭目標、手段、強度等的有限性,體現了從技術到戰術的持續進步。研究軍事需要反復研讀戰史、體味戰史。當然,歷史不是現實,更不是未來,從來沒有兩場完全相同的戰爭。我們研究戰史,不是為了尋找某種相同性,而是從歷史的真實中尋求感悟,激發基於新的時代條件的創造性思考,盡力把握那個不確定的未來。
實際上,《孫子兵法》十三篇,就非常善於運用戰史說理﹔毛澤東一生圈點、閱讀《資治通鑒》17遍,並說“《通鑒》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採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証法”﹔拿破侖總結戰史戰例,形成自己的戰略戰術﹔克勞塞維茨除3卷《戰爭論》外,還有7卷戰史戰例著作﹔馬漢享有盛名的“海權論”,主要體現在三部戰史著作之中﹔利德爾·哈特的《戰略論》一書,戰史內容超過四分之三,而且他還著有兩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等。戰史讓偉人大家變得智慧,我們也應當充分借鏡思維。
我們熟悉的戰史,一般框架主要由時代背景、戰爭起因、戰爭雙方、戰爭指導、戰爭過程、戰爭結局、戰爭影響、經驗教訓等組成。近些年學界拓展戰史研究,開始關注戰爭與國際政治、戰爭與國內政治、戰爭與經濟、戰爭與社會、戰爭與文化等,推出了可喜的成果。需要不斷深化這些主題,還可以尋找更多新的視角。比如,戰爭與金融,戰爭與科技,戰爭與法律,戰爭與倫理,戰爭與心理……每一個新的視角都是一扇新的窗戶,能夠看到僅從大門裡看不到的光景,感悟到許多新的事理。
戴爾·科普蘭的《經濟相互依賴與戰爭》一書,讓我們重新思考有關中美經貿聯系密切是兩國關系壓艙石的說法,今天中美貿易沖突讓人真切地感受到壓艙石有時可能成為風險源。杰弗裡·帕克的《劍橋戰爭史》,讓我們進一步認清了戰爭發動者經常抱著“速決夢想”,實際上卻陷於持久、歸於失敗的殘酷,一戰如此,二戰也是如此。格溫·戴爾的《戰爭》一書,讓我們知道,美國參戰士兵在200到240個“戰斗日”之后就有可能精神崩潰,而英國軍隊因為參戰輪換較為頻繁,士兵精神崩潰的時間會出現在400個“戰斗日”左右。尼爾·弗格森的《世界戰爭與西方的衰落》,讓我們領悟到由歷史學家來解釋“人類對人類不人道”是多麼深刻和可怕,聯想到未來可能出現的“機器對人類的不人道”,更需要我們有一種哲學的思考。
前一段時間,歐洲很多國家都在做一戰百年紀念,他們對一戰的紀念重在喚起和強化一種記憶,這種記憶是與大量墓碑和遺骨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記憶更多刻錄著戰爭的悲慘、和平的可貴,而不再主要糾纏於敵我之間的是非恩仇。據記載,1914年的聖誕節,英國和德國士兵在戰場上聯歡,當時兩支白天還在相互對射的部隊,到了晚上都放下武器,走出戰壕,為一名德軍士兵唱生日快樂歌和聖誕頌歌,點亮大片的燭光,還踢起了足球。而在此前的6個月中,兩軍相互殘殺,已經死了100萬人。戰爭中總是充滿諸如此類不可思議的事情,它們顯然也是戰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都需要進入戰史研究的視野。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广东企业如何打通全球产业链?
-
港澳台企业抢滩中博会,同绘大湾区发展蓝图
-
北京市政协委员黄轶:需关注科创企业困境 多元
-
湾区机遇,为企业成长提供重要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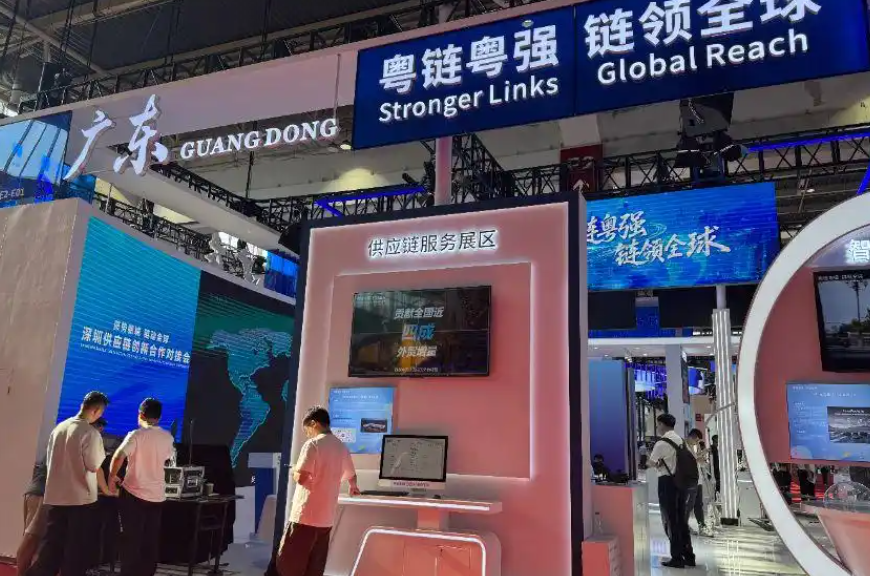



 热点新闻
热点新闻